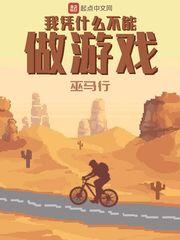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五十七(第2页)
……
八月十四这日,桓煊下了朝,骑马回到常安坊,如往常一样将自己关在鹿随随曾经住过的小院中——匾额碎了,如今那院子没了名字,可一院子的海棠花仍旧在那里,冷冷地、讥诮地看着他,简直要把他逼疯。
高嬷嬷亲自提了食盒来,在门外小心翼翼地劝道:“殿下,多少用点饭食吧,若实在没胃口,喝几口汤羹也好。”
桓煊隔着门道;“孤不饿,嬷嬷去歇着吧,把院门关上。”
高嬷嬷在门外站了半晌,叹了口气,终是转身离开了。
桓煊执起案上的酒壶,注满一杯,拿起来抿了一口,酒早已酸了,他腹中空空,酸酒灌下去就像有只手在他腹中搅动,可他不觉得难受,甚至觉得心里舒坦了些。
这是鹿随随为他酿的庆功酒。
一杯接着一杯,一壶酒很快就见了底,酸酒也能醉人,可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他合衣躺在榻上,抱紧鹿随随留下的青布大绵袍——他总是嫌这身衣裳丑,可这身丑袍子却是唯一一件不属于阮月微,只属于鹿随随的东西。
他怔怔地望着帐顶,帐顶上也织着海棠花纹,他的眼前有些恍惚,那些海棠花便晃动起来,冲他眨着眼睛,讥嘲之意更甚。
他忽然忍无可忍地坐起身,大步走向门口,用力推开门。
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黑了,空中无星也无月,夜色那么黑,那么暗,像化不开的浓墨,仿佛永远不会再亮起来。
廊下的风灯摇晃着,投下昏黄惨淡的光,光晕里是一棵名贵的海棠花。
桓煊从心底窜出一股怒火,他从腰间拔出一把长刀,向着海棠树劈砍下去,海棠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呼,拦腰断成两截,竟有黑色的血从断处汩汩地流出来。
桓煊心里一惊,定睛一看,那淌出的不是血,却是火油。
火油淌了遍地,流到庭中,又顺着台阶漫上去,覆盖了廊庑,然后灌进屋子里。
桓煊忽然明白过来他该怎么做了,他欣喜若狂,摘下一盏风灯,用手杂碎了琉璃罩,取出蜡烛投入屋子里。
“呼”一声响,火蛇窜起数丈高,很快顺着门框、房梁、柱子蔓延,海棠花的平荫,海棠花的帷幔,海棠花的几案、床榻、屏风全都烧了起来,整个院子成了一片火海。
他站在庭中忍不住笑起来,那些折磨他的笑眼终于都在火海中化成了灰烬。
就在这时,屋子里忽然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些许沙哑,但无比动人,像绢纱在耳畔温柔地摩挲,可那个声音此时却在哭喊:“殿下,殿下,你为什么要烧死我,桓煊你好狠的心……”
桓煊心中大骇,他站在火场中却如坠冰窟,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暖意。
他转身冲进火海中,果然看见鹿随随正坐在床上哭。
他忙向她奔去,眼看着只有咫尺之遥,却听轰然一声,一根燃烧的横梁砸下来,横在两人中间。
“别怕,我救你出去。”
桓煊往火中走去,火舌舔着他的双脚,很快他的双腿都燃烧起来,发出难闻的焦味。
可他却没什么知觉。
“别害怕,我救你出去。”
桓煊望着随随道。
鹿随随的脸在火光里扭曲起来,明明在哭,看起来却像在笑。
“殿下,你说过从此不会叫我落单的。”
她轻声道。
桓煊心口闷闷一痛:“是我的错,我们先逃出去。”
“你自己去吧,我不跟你走了,”鹿随随道,“我要回秦州去找我阿耶阿娘。”
“别说傻话,你阿耶阿娘早就过世了。”
桓煊伸手去够她。
可分明近在咫尺,他却抓了个空,她像影子一样飘来飘去。
“那我也要同他们在一起,”鹿随随轻笑了一声,“殿下你走吧,火烧起来了。”
桓煊道:“你跟我一起走。”
随随摇摇头:“殿下忘记了?
宠妃的演技大赏
上辈子,世人都说苏菱命好,姝色无双,又出身高门,父亲是镇国大将军,兄长是大理寺少卿。十七岁嫁给晋王为妃,两年后又顺理成章做了大周的皇后。若论尊贵,真是无人...
此情难言
每个女人,都期望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我也一样。今天,我嫁给了爱了十二年的男人,只不过,用的是我姐姐秦佳梦的名字...
午夜开棺人
棺材镇可咒人数代的奇葬白狐盖面腐尸村可使人永生的镇魂棺郪江崖墓所藏可致阴兵之牧鬼箱成都零号防空洞内的阴铁阎王刃开棺人的诡异经历,环环相扣步步惊心,为您揭开中华异文化诡事!...
热血狂兵
...
我凭什么不能做游戏
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你向前走一步,你创造的,可能就是历史!加入我,给那些拒绝你的人看看,曾经的他们是多么的有眼无珠!那一年。在燕京人才市场无...
十方武圣
末日荒土,世宗三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中央皇朝崩坏,各地群雄割据,门派独立。魔门妖党隐于暗处作乱,帮派相互征伐,混乱不堪。天灾连连,大旱,酷寒,暴雨,虫灾,人民苦苦挣扎,渴求希望与救赎。大乱之中,各...